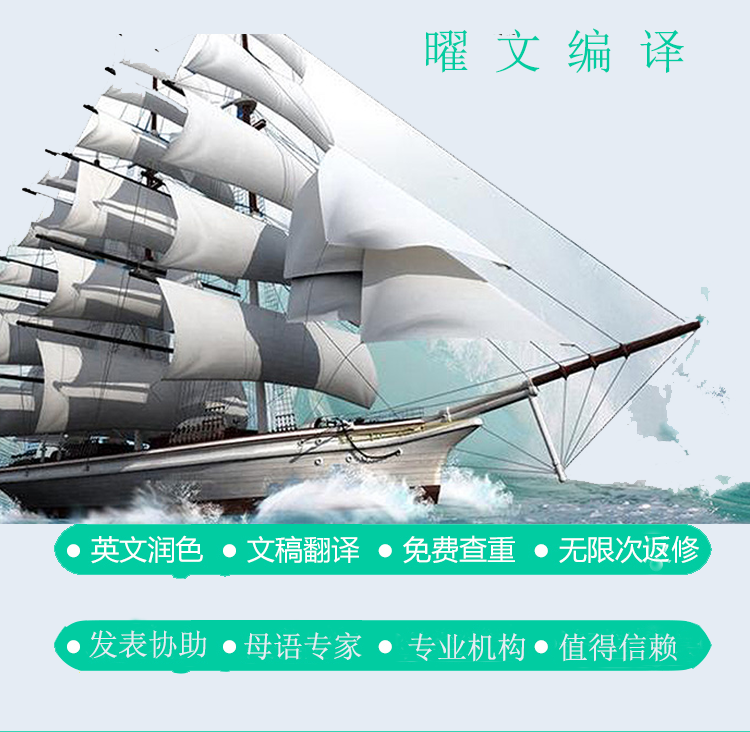曜文编译致力为大家分享更多更好的高质量论文,供大家学习参考。同时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转载的方式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观看学习,从中获得经验和灵感,小编将为大家提供*新论文资讯。
一、作者及本书简介
傅天仇(1920.3—1990.8)是我国**代著名雕塑家,美术教育家,原名傅健朝,笔名傅路,广东南海人。1942年毕业于桂林美专,深为校长、著名金石书画家马万里赏识,继而被推荐给来校授课的徐悲鸿。傅天仇创作了著名的浮雕《武昌起义》、南开大学内的周恩来铜像。傅天仇十分重视对我国古代传统雕塑的研究,大力提倡抢救古代传统艺术遗产,将中西艺术结合,使雕塑的移情性得以发扬,创作出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新雕塑。从世界范围看,不同的视觉造型语言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意义。如方闻、巫鸿等学者的研究,致力于指标性的视觉文化机制,寻找视觉文化内在性的历史逻辑和形成原因,梳理中国艺术的个性基础。傅天仇本人也是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对象,《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一书对于了解中国雕塑的内在理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他从一名杰出的雕塑家视角出发,生动地描述了中国雕塑语言的特质,用贴切而生动的叙述方式梳理了中国雕塑特有的历史。其中有几篇对于汉代雕塑的描写非常精彩,对于霍去病墓及古代战马雕塑反复描写,不仅透露出作者对它们的重视,且从雕塑家的视角佐证了这些艺术品在中国雕塑史上的地位。《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是傅天仇的文集,其文章之间并无时间顺序及行文逻辑,讨论的主题多变,并有一定的重复性,总体而言,是在探讨中国传统雕塑以及当前创作的现状,可见傅天仇对于雕塑艺术研究的使命感。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此书流露出一定的民族情感先行论,但是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所做的努力自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二、此书著述亮点及笔者获得的启发
首先,傅天仇在文中反复强调了创作主体对于呈现雕塑艺术风格的作用,他在《天龙山石窟的雕塑艺术》中提到,这些石雕的作者多是勤劳朴素的劳动者,使我们体会到古代艺人在规定的题材中表现人的情感、认真观察生活和研讨技艺的情况。傅天仇将描述的视角投向创作主体,其情感真实而鲜活。作为雕塑家,他明白创作过程的艰辛及创作状态的拿捏,也即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必须保持朴素的情感才能使作品打动人,具有移情的功能。笔者认为,创造性的劳动古今一致,雕塑创作所依赖的材料、条件、环境、体力等,决定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及生存状态。傅天仇亦明白一个人的创造力来自创作者的天赋和他所处的生活世界。画像砖中带有创作者的习惯与观念,他们对人物道具的观察、对不同社会阶层角色的理解,都反映出画像砖的制作者当时的认识。这些容易被艺术史家忽略的群体,基本不在研究者的视线范围内。由于傅天仇长期从事雕塑的创作、研究、教学,他才会有如此清晰而真挚的“移情”表述。其次,作为雕塑家对于中国传统雕塑的理论性发掘。目前对中国传统雕塑作系统研究的历史较短,缺乏对雕塑专门、精深的理论研究。近代的学术研究又多是从翻译外来学术成果开始的,无论是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是语言自身的不同,都难有精炼性的语汇对应中国雕塑的审美特质,傅天仇关于龙门石窟“平”“亮”“怪”“短”的描述是比较具有创造性的。傅天仇对“亮”进行了丰富的描述,既有对于佛像雕塑的独到理解,又透露出傅天仇较强的实践技巧。这些规律是他在长期创作过程中提炼出的。傅天仇不仅创造性地分析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内在规律性,而且解释了它们让人产生快意的原因。中国的佛教造像,尤其是石窟雕塑,有很多比例不准确的例子,如龙门石窟、云岗石窟等,大多为比例失调、头部过大,感觉比较奇怪。傅天仇在论述传统佛像中“短”的概念时,从正反两方面解释了原因,回答了很多人对于雕塑比例缩短的疑惑。遗憾的是,傅天仇没有将自己总结的规律放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进行比较分析。佛教雕塑在写实的手法基础上,为了获得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效果,进行了比例的处理,有意做短。细致品读,《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中有很多精彩而富于启发性的描述:“以前看过这些雕刻的人说,他在乱石中发现了一件好石雕,可是回头找朋友来看时再也找不到石雕了。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只要看的光线和角度不同,顺石造型一类的雕刻很容易被忽略。”①36近代以来,对于汉武帝茂陵石刻艺术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单体开始的。因历史久远、地震损坏等自然、人为因素,这些石雕脱离了它们原始的整体性,被重新摆放排列后,尽管作为独立的单件雕刻仍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精品,作为整体性的意义被忽略了,其原初观念也变得难以把握。笔者对傅天仇在书中的一段描述印象深刻,增强了他对雕塑风格的进一步理解。傅天仇对茂陵石刻的研究具有独创性,遗憾的是他没有对祁连山作进一步的考证②。傅天仇将自己置身于创作者的立场讨论作品的艺术性,行文中自觉地流露出雕塑的制作过程、创作要求及自身修养等因素,丰富了读者对于雕塑艺术的理解,也让笔者对作为雕塑家的傅天仇的认识更加深入。虽然我国有丰富的雕塑遗产,但由于相关文本文献的缺乏,对于中国雕塑的书写研究困难较大。相比之下,中国书画的书写已成体系,不论是宫廷书画,还是文人作品,都有历史传承及文献体系,是精英阶层的文化活动。而雕塑从业者多为底层匠人,他们在艺术发展史的书写上不受重视,更无能力书写自己的方法论,这造成了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困难。中国雕塑历史悠久,作品丰富多样,具有历史史料价值和艺术性,然而对中国雕塑的研究不如中国书画,这与“文献中心主义”的学术规范有较大的关系。同时,中国雕塑的发展脉络纷繁复杂,主线难以梳理把握,当前课题是如何建立系统的中国雕塑学术研究方法论。傅天仇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他能够进入雕塑作品内部剖析艺术形式及风格特点,这种将自己的创作体会融入古代作品的著述方式给了笔者很多启发。傅天仇身体力行地探索中国雕塑的内在理路,笔者也有致力于对中国雕塑进行深入研究的构想。艺术史是对于艺术作品及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的发现与建立。傅天仇欲以“移情的艺术”统揽古代中国雕塑发展的内在精神基础,以雕塑家的视角与情怀,厘清中国雕塑的自身价值体系。中国雕塑不是物态化的表象,有着丰富的精神性。这种注重体验的写作方式,正是美学要关注的对象。
三、中国雕塑主要著作之比较
对于中国雕史的著述,比较突出的有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王子云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汝信主编的《中国雕塑》、王朝闻《雕塑美学》、贺西林《寄意神工——古代雕塑》、孙振华《中国雕塑史》等。王子云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不仅详实全面地收载了中国的雕塑遗存,而且深入每一处亲自测绘考察,加上他作为修养较高的雕塑家身份,其艺术眼光的标尺是很精准的。这本著作是填补业界学术空白的里程碑。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是一部严谨的雕塑学术著作,其用历史学的框架梳理了中国雕塑的发展脉络,语言精练,内容丰富,在简短的描述里,足见作者的文献功力与论述力度。遗憾的是,全书仅做了简单的雕塑历史分期的工作,并没有对各个时代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总结,也没有对中国雕塑作理论性的发现。汝信主编的《中国雕塑》在考察对象方面做了更详实的整理,历史分期更加清晰,较好地构建了风格变迁的线性时间。汝信的学术功底及艺术素养深厚,能清晰地从各个时代的哲学背景对中国雕塑进行归纳、分期,使读者容易捕捉到书中的逻辑。然而,他并没有进入雕塑作品的内部进行分析,如风格的成因、材料的特性、雕塑技术及工具的发展与使用等,尤其对于现代雕塑的描述,没有把握住学院雕塑何以出现的内因,以及学院雕塑家接受的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造型训练体系,仍然只停留在外部的观看与分类上。王朝闻的《雕塑美学》试图从美学角度分析和构建中国雕塑的审美体系,这种努力的动机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此书的理论性不强,行文结构较松散,论证不紧凑,多为个人感想式的的散文集,学术性的构架不强烈,致使读者很难把握中国雕塑的内在结构。贺西林的《寄意神工:古代雕塑》相较于汝信主编的《中国雕塑》,规避了现代学院雕塑与中国古代雕塑的割裂,意识到二者的冲突与不兼容性。然而,书中雕塑类型的选取基本是考古墓葬和佛教寺庙、石窟造像,美术史分类的痕迹较重,难以让人走进中国雕塑的内部,是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外部风貌进行的一般性描述。孙振华的《中国雕塑史》试图为各个时代的雕塑做更深入的风格区分,细分为宗教雕塑、明器雕塑、陵墓雕塑、纪念性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和工艺雕塑等。这种细致的分类工作能使中国雕塑的属类有了更明晰的类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雕塑研究的书写模式,但作者只是进行框架结构上的梳理普及,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创建,也没有在实践考察方面投入更多的心力处理新材料,只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摘录。这些学者为中国雕塑及中国雕塑史的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打开了解中国雕塑艺术的大门,但是对于中国雕塑的核心价值及美学资源的挖掘仍有很大余地,所触及的关于中国雕塑的实质性问题不及傅天仇在《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一书中深刻、明晰。从这一点看,中国雕塑的研究还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用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对其进行理论性构建与挖掘,就现状而言,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尚有发展空间。
四、此书不足之处及笔者思考
首先,作者的创作思想受限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多数杰出的作品以及伟大的思想是回应时弊的,新时期的学术热潮,加上民族意识的高涨,对于自身文化的研究梳理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然而,傅天仇没有西学背景,也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写作训练,难以深入了解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思想,也没有使用与西方汉学家对话的研究方法,导致他的宏愿变成了自言自语式的抒情。《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中的部分文章缺乏对西方世界艺术文化的系统性认识。这与王子云构筑《中国雕塑艺术史》是一致的,王子云开宗中国雕塑史的写作是有拓荒意义的,是后学难以超越的高峰。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史的框架理论构建雕塑发展的内在理路,导致其学术分析忽视了中国艺术特有的精神性。而傅天仇具有强烈的“走自己的路”的自觉意识,并试图找到中国艺术主体性的价值体系,“南北朝早期造像,重视气势与神秘感,到龙门期造像,则以整齐装饰性衣纹及写心著称,这些动态近似,但重视表现内心深度的造像,正是秦代雕像的遗风。至于浮雕的飞天,伎乐的层次与衣纹处理,却似汉代画像砖石的韵味。至于龙与羽人在南北朝佛教石窟中的出现,更是雕塑中国化的证明”①10。作者没有进行客观的考证比较,也没有对风格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有效的考察,因而难以使读者产生形象化的理解,雕塑中国化的观念也不能让人产生可靠的信任感。在描写茂陵石刻的布置时,傅天仇强调多样性不是为了形式,而是为了要加强祁连山的意境,尽管解释合情合理,但缺乏文献的考证支持,不免有失说服力。
五、中国雕塑研究应投向更开放的视域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专门探讨艺术时接受了当时可能已经流行的艺术模仿现实或生活的观点,为我们如何超越个人局限、时空差异等因素研究古代雕塑,建立审美通感启发很大。作为一个整体,诗意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且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人有模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在于人善长模仿并能通过模仿获得知识。其次,人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不仅是诗艺产生的原因,而且是与人的行为有关的所有艺术形式,雕塑艺术同样不例外。叶朗在讨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美在意象”的理论创造时说到,中国艺术家追求“意境”,“意境”就是艺术作品显示一种形而上学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对于中国雕塑的深入研究,需要有中国学派的美学体系进行分析描述。叶郎强调中国特色的美学学派要注重吸收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等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撇开他们是违背人文学科的发展规律的。意象的世界是人的精神创造,它不仅存在于人的审美活动,而且存在于人的艺术创造过程。学界应该对中国雕塑史中的经典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树立坐标轴,如兵马俑、麦积山泥塑、双林寺宋代泥塑等名作,思考是否可以借鉴书法史及书法理论的研究方法,从书法用笔,如锥画沙、屋漏痕等经典范式中汲取营养。感性的视觉形象进入了书法绘画的语言体系,得力于知识精英的书写方式及话语权,传统雕刻技艺讲究口传心授,如何把握程式化的口诀传承以及个体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雕塑创作,如果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性构建,中国雕塑经典中所蕴含的特有价值就难以被揭示出来。笔者赞赏傅天仇在《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的研究思路,此书为有志于中国雕塑创作的实践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中国雕塑的理论与实践应从“走自己的路”跨越到“走出自己的路”,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价值被忽视,学界有责任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六、中国雕塑艺术的复古创新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连续性文明,就时间性而言,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同样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纵观商周以来的雕塑艺术,雕塑风格演变的连贯性,是对外部因素的吸收作自身主体性的反观,这才是中国古代雕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巫鸿在《时空中的美术》中谈到梁思成作为建筑史家与建筑设计师时的身份差别,“身为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他把自己对中国现代建筑的理想与一个更古老的历史阶段(即他的‘豪劲’时期)相联系,有意识地排斥二者之间的中间阶段的建筑风格”③。巫鸿以“复古”的感知模式,结合“现代”审美需求,创造出跨越年代断裂的回眸性的历史联系。“复古”观念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在历代艺术理论家的讨论中,论者常把元代初期的赵孟頫作为推动复古潮流的重要人物,他创造了丰富的作品和理论。复古是对传统的追摹与反思,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笔者通过对中国传统雕塑的研究,梳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及创作方法,这是理解中国雕塑艺术与造型原理的有效途径。秦汉以降,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走向了平行发展的各自不同的路线,尤其是汉代雕塑艺术中对于气韵、意象的传达,与希腊罗马雕塑艺术中的理性结构完全不同。这种注重主体的心灵感受和外部气韵的艺术观念在唐宋以来很好地继承、发展。通过形象化的处理,人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出中西方雕塑艺术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背景下平行发展的审美体系,二者在历史发展中有交叉融合,彼此见面发展,没有断裂。对中西方雕塑艺术发展的比较与研究,如果没有把握住各自的逻辑流变,是很难做出客观具体的研究成果的。中国雕塑史有着丰富的资源,当代学者必须以“开放”与“多元”的国际视野追求“复古”。中国的雕塑艺术如何向丰厚的传统文化遗存中汲取营养?如何在发挥历史资源优势的前提下推动雕塑艺术创作的传承与创新?学界应身体力行,避免流于表面性的利益驱使,要将自己的真实情感投射到中国雕塑艺术的研究上。傅天仇在《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一书中的努力,为中国雕塑艺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具有价值的尝试。中国雕塑的发展不仅需要雕塑家的创作热情,而且需要一批严谨的雕塑艺术史论家及雕塑艺术批评家从艺术史、艺术哲学等角度,多元思考、梳理、构建中国雕塑发展的脉络以及审美特质,从而推动中国雕塑的研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为雕塑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感渠道,而且为世界文化注入了中国艺术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
[2](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
[3]叶朗.叶朗自选集:意象照亮人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陈玉
声明:本文转载于网络,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站致力于为大家 提供更多,更好的新闻内容。曜文专业,专注,为您提供SCI论文润色,发表服务。